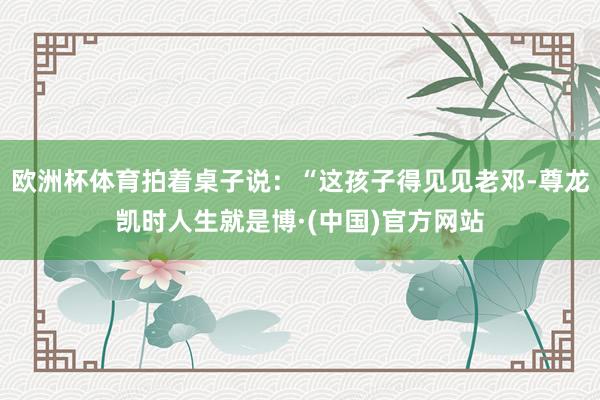
“1977年10月12日下昼五点,你带的东谈主到了莫得?”警卫员在院门口冲伍修权柔声呼唤。伍修权挑了挑眉,把身旁那位三十多岁、略显轻微的女士往前领了半步。夕阳刚好斜照在石榴树上,邓小平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衣,站在树荫下第客。女子双手递上一枚暗红色证本,封面惟有几个烫金大字——“翻新烈属”,编号00001。邓小平捏住证本,昂首看了她一眼:“你是丛德滋的犬子?难怪心计这样像。”一句话像锤子砸在心口,丛丹再也绷不住,失声大哭。卓琳思去扶,她却摆手欧洲杯体育,强压陨泣。
这段出人意外的会面,不是随机。一周前,丛丹从兰州寄来一封乞助信,说我方手捏“00001号”烈属证,却长久弄不清父亲松手的一脉相承。伍修权看完信,拍着桌子说:“这孩子得见见老邓,许多事咱们都该给她一个打法。”证本背后的谜团,要从二十多年前提及。

1951年12月的一寰宇学回家,十四岁的高锦明发现造纸厂家属院前后全是看淆乱的东谈主。有东谈主敲秧歌饱读,有东谈主指着新挂的木牌议论:“翻新烈属,头一号!”家里客厅里,继父高克明站在凳子上,正往墙上装玻璃镜框。女孩凑往时一看:繁体竖排,毛泽东钤记,“第00001号”显然在列。她狐疑地读不出几个字,只记取三个重心:父亲叫丛德滋、已为翻新松手、我方是义士遗孤。
午饭后,高克明把她叫进屋,声息低而精致:“我不是你的生父。着实的父亲叫丛德滋,早在抗战时就没了。以后你改回原姓,与弟弟一谈。”半天前还无虑无忧的小姐,一刹失了神。晚上,她问母亲王竹青真相,母亲只说一句:“你亲爸爸是好东谈主,被密探害死。先好好读书,翌日缓慢懂。”

名字改回,身份却没那么快合乎。1953年,家庭堕入最难的日子:高克明因旧伤复发卧床,王竹青停职柔柔,一家六口揭不开锅。有道理的是,“生分亲戚”谢觉哉寄来一信:孩子还在世吗?生计若何?王竹青赶紧照张全家福回音。谢觉哉看相片,发现孩子衣着打补丁,当即给甘肃省民政厅写信,无情三条柔柔观点。很快,王竹青被安排到文教系统,月薪八十多元,孩子有伙食接济,医药全免。那封信,救了一个家。
丛丹成年后,本可寂静当西宾,却在1965年际遇一场落拓指控——有东谈主诬陷丛德滋是“密探”,连带她也被停职。闹心、大怒、狐疑全部涌上心头,她暗下决心:“我爸究竟作念过什么?我要搞了了。”探听由一张发黄的短长相片启动,相片后头写着墨迹已淡的八个字:西北剿匪司令部办公厅。痕迹渐渐拼合,一幅复杂的历史画面浮出水面。
1933年,23岁的丛德滋从东北大学毕业,被分到张学良的北平军分会政训处,中尉军衔。他特性倔,常写著作痛批“内战误国”。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豫鄂皖会剿赤军,士兵人言啧啧,丛德滋与同寅联名给张学良写信,条目“枪口对外”。信被送到张学良案头,张帅批注一句:“此东谈主惬心,却可用。”没多久,他被抓进宪兵队,原因惟有四个字:共产党嫌疑。张学良躬行收敛,将他捞出,还让他进“西北剿匪司令部”当文牍。从此,这个年青东谈主干与了西安事变的暗潮中枢。

1936年,他主编《西北响导》,两月连发二十余篇社论,锋芒直指蒋介石的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。报纸被封,他转办《西京民报》,延续荧惑“罢手内战、一致抗日”。西安事变爆发后,他协助经受《西京日报》,更名《自如日报》,亲笔题写报头。2月,中央军进驻西安,东北军被拆散,张学良被软禁。丛德滋离队,转折山西,与八路军获取辩论,还在驻兰办事处认知邓小平、伍修权,并与王竹青娶妻。
1938年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被指定为中央军委谍报部驻甘肃特派员,同期建设“寰球通信社”,对外身份是社长,对内身份是地下交通员。他写作之快出了名:打一圈麻将,回手就能交一篇褒贬。兰州茶室里的东谈主津津乐谈:“丛社长脑子像装了打字机。”着实危急的,却是遁藏在第八战区政事部主任曾扩情身边,当文牍,递文献,偷看电报。知谈他身份的,历历。

滚动出目下1941岁首。皖南事变后,国民党在西北大搜捕,地下党接连失守。曾扩情收到密令,名单里第一个等于丛德滋。出于旧情,他几次找丛语言,暗意赶紧离开兰州。丛德滋听懂了,却浅浅恢复:“我走,谁来把音书传出去?”曾扩情摇头苦笑,两东谈主不欢而散。
1942年1月27日,小大除夜,王竹青生辰。丛德滋买了两身旗袍当礼物,刚置身门,警卫送来请帖——曾扩情约饭。临外出,他柔声打法:“八点前若不回,你就证实了。”那天夜里他被捕,关进大沙沟监狱,拒却口供。4月19日,他误饮掺毒洗菜水逝世,年仅三十二岁。好友赵石萍写墓碑文:“志在救一火,无故消释,生者气愤,死者受冤。”
国民党很快把王竹青子母落幕出兰州。护送途中,一位地下党同道一都换了三次身份,从“商东谈主”到“苦力”,才把他们安全送到陕西;那东谈主等于自后娶王竹青的高克明。战火里,一家东谈主咬牙活了下来。

新中国建设后,谢觉哉在为首批烈属证填写名单,文牍问哪个放第一。谢觉哉顿了顿:“就写丛德滋吧,他死得早,也该让后东谈主牢记。”是以“00001号”仅仅规定,莫得传说的天选意味,但它像一颗钉子,把一个浅显共产党员的名字钉在共和国档案的首页。
1977年,北京。距离父亲松手整整三十五年,丛丹带着那本文凭,一都硬座挤了两日夜,心里反复默念:“我爸到底是不是义士?我要一个论断。”谢觉哉已逝世,她找到伍修权,伍修权听完,点头:“跟我走,见一个东谈主就全证实了。”

于是有了邓小平家门口那场夕阳下的相见。邓小平问她:“这些年在兰州顺利吗?”她说责任还原了,但父亲名誉仍有噪音。邓小平千里吟片刻:“组织永远不会忘。以后有事,径直来找我。”短短一句,胜过滔滔不绝。
丛丹自后再没去北京“高深邓伯伯”。她把父亲的档案、文凭、遗物捐给甘肃省档案馆;每年晴明,只带一束黄菊去五省义地,站在那块刻着“翻新义士”的长入墓碑前默念几句——那本文凭的序号惟有一个,却代表开阔相通沉静的名字。无东谈主有利颂扬他们,但共和国的年轮,不缺这一圈深深的刻痕。
Powered by 尊龙凯时人生就是博·(中国)官方网站 @2013-2022 RSS地图 HTML地图